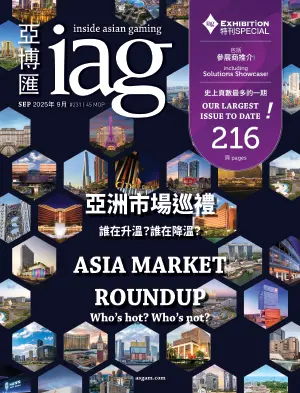前新南威爾士州監管官員Paul Newson質疑:澳洲博彩業長久以來的監管思路當下是否仍具現實價值?
澳洲博彩業的誠信監管體系,是上個時代監管邏輯遺留下來的「產物」。其根源可追溯至《Street 報告》與《Connor 報告》兩份奠基文檔,當初設計的核心是為防範黑社會勢力滲透業界,並且大量借鑒拉斯維加斯的監管思路。這兩份報告建議參照美國模式,建立起專屬發牌制度,將「對個人展開嚴格審核」作為博彩業誠信的核心——包括審核範圍涵蓋財務背景、人際關係與個人品格等維度。
 然而,曾經合理的防範機制,如今已淪為過時的「鐵律」。澳洲博彩業當下面臨最大的誠信威脅,並非企圖潛入博彩場所的犯罪分子,而是源於業界根深蒂固的治理機制失靈、道德底線漸失,以及「利潤先於原則」管理策略三大問題。
然而,曾經合理的防範機制,如今已淪為過時的「鐵律」。澳洲博彩業當下面臨最大的誠信威脅,並非企圖潛入博彩場所的犯罪分子,而是源於業界根深蒂固的治理機制失靈、道德底線漸失,以及「利潤先於原則」管理策略三大問題。
時移勢易,防範機制嚴重脫節
震驚澳洲的多宗重大博彩醜聞,如今已是街知巷聞。當前業界的核心議題是「轉型」—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皇冠集團(Crown),目前該集團已重新定位為「道德領導力樣板」。其內部推行的行動準則——「問應不應該做,而非能不能做」已成為業界重塑誠信、重建信任的文化轉型符號。

皇冠集團的轉型之路,揭示了改革的關鍵切入點:領導層問責機制、風險文化培育與道德治理體系。但這一過程也暴露出誠信監管體系的現實矛盾——它仍執着於審核個人背景,而非聚焦企業行為,與業界現狀出現嚴重脫節。
初衷已失,監管框架名存實亡
現行誠信監管體系不但「入侵性強」,運營負擔沉重,其合理性也越發不足。申請人(尤其是跨地區經營者)必須忍受反覆且繁瑣的個人事務審核,而審核過程往往忽視實際風險,亦不考慮當代企業的經營背景。「跨地區認可」機制極為罕見,監管機構耗費大量資源去核實信息,往往大部分與違規行為的真正誘因毫無關聯。
數十年前,《Connor and Street Reports》提出的「嚴格監管防範犯罪滲透」,本是時勢所需,但如今的監管模式仍停留在以「Bugsy Siegel為假想敵」的階段,完全脫離現實——當下的違規行為已經是來自董事會會議室,而不再是暗巷密室內。業界最大威脅已轉為內部問題,即「法律最低標準主義」文化、董事會的漠視態度,以及不道德的領導決策。
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監管失靈證明了,問題從來不是出自「審核不嚴的個人」,而是源於有害的企業文化、利益衝突的薪酬體系、董事會監管缺位,以及監管機構的疏忽。這類風險無法通過「誠信審核清單」篩除,必須依靠系統化治理與領導層引導。
 投入過時,回報遞減枉費期待
投入過時,回報遞減枉費期待
更令人擔憂的是,在成熟且以企業化運作為主的市場中,依賴「前置高門檻個人誠信審核」的風險緩解方式,早已成效慘淡。這種過度複雜的「入門關卡」,完全忽視了業界對「智能化常態監管」與「靈活監管工具」的需求。
澳洲在「更新這一傳統框架」上的政策投入幾乎為零。該體系得以延續,僅僅是因為慣性使然,而非能帶來可衡量的成效。監管行動往往缺乏創新,部分監管機構仍將「完成審計或調查的數量」視為業績,彷彿數量本身就等同於影響力。這實質就是「監管表演」——用表面行動冒充實際成效。
業界真正需要的,不是更多表格與審核環節,而是更明智的監管互動。監管機構必須轉向「情報驅動、風險導向、結果為本」的模式,明確真正的漏洞所在,及早介入干預,並在「能推動文化轉型的領域」施加影響,而非僅僅的「打個勾,功課了」。
 事實可證,安於故俗溺於舊聞
事實可證,安於故俗溺於舊聞
維多利亞州針對墨爾本皇冠賭場的皇家調查委員會揭露,其一大堆違規行徑,如欺騙、洗錢、脅迫監管機構,以及剝削弱勢賭客。這些行為的幕後推手,並非「有黑歷史的個人」所為,而是「容忍道德投機與法律最低標準主義」的董事會所作之因。
另一個極其惡劣的案例來自星億賭場(The Star)。該賭場協助顧客使用銀聯卡,將賭博消費偽裝成酒店住宿費用。這一操作讓顧客規避了「內地發行銀聯卡不得用於博彩消費」的限制,是需企業層面協調的「道德失準且可能違法」的規避手段,體現的是戰略意圖,而非誠信審核的疏漏。
金融業的案例也與之相似。2018年針對澳洲聯邦銀行的審慎調查發現,該行存在大範圍合規失靈與文化頹廢問題,根源並非「個人誠信缺失」,而是「領導力不足、風險治理缺位與內部監督失效」。
 這些失敗案例帶來的啟示清晰可見:道德崩潰很少取決於「誰通過入門審核」,而是取決於「一旦進入企業,哪些行為能被容忍到甚麼程度」。
這些失敗案例帶來的啟示清晰可見:道德崩潰很少取決於「誰通過入門審核」,而是取決於「一旦進入企業,哪些行為能被容忍到甚麼程度」。
識明智審,對應風險應對未來
現行誠信監管體系未能通過「結果測試」,它不但加重申請人負擔、阻礙有效投資,還將監管資源浪費在低影響的審核上。改革早已刻不容緩,具體應包括:
- 簡化與統一流程:建立跨地區認可機制,減少重複審核
- 轉變關注重點,從「個人風險」轉為「企業風險」,聚焦治理模式、企業文化與道德立場
- 優化監管資源,將資源更多投入在「早期識別風險、風險畫像構建、行為與文化情報分析」
- 認可企業進步:對已開展深度改革、實現道德轉型的企業,認可其領導層的成熟度
誠信的重要性不變,但評估與保障誠信的方式必須與時俱進。
結語
基於「傳統恐懼」的誠信審核,已無法應對當前的風險格局。它不僅回報遞減、分散監管重心,還成為業界創新與提升的絆腳石。
更糟糕的是,這折射出更普遍的監管弊病——即「以數量為導向的檢查計劃」被奉為業績,而無視實際影響。宣稱「完成500次審計」聽起來頗為亮眼,但如果這些審計僅是核對機器標籤或行政合規性,那我們衡量的只是「行動量」,而非「實際成效」。
 這種表面化的監管互動,擠佔了更有意義的監管工作:構建精密的情報體系、有效監控高風險行為、清晰傳達監管預期。從歷史上看,博彩業的監控機制從未有效形成威懾,也無法即時洞察新興風險。要推動業界真正提升,監管機構必須從「打勾式監管」轉向「風險信號式監管」——主動識別脆弱環節、引導改革方向,將監管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領域。
這種表面化的監管互動,擠佔了更有意義的監管工作:構建精密的情報體系、有效監控高風險行為、清晰傳達監管預期。從歷史上看,博彩業的監控機制從未有效形成威懾,也無法即時洞察新興風險。要推動業界真正提升,監管機構必須從「打勾式監管」轉向「風險信號式監管」——主動識別脆弱環節、引導改革方向,將監管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領域。
業界監管的未來,不在於細查個人銀行的流水帳,而在於審視董事會與高層管理層的行為、企業文化與激勵機制。要實現這一目標,必須以「有效監控實際行為」為基礎,並讓監管行動緊扣「對最大風險所在的清醒認知」。